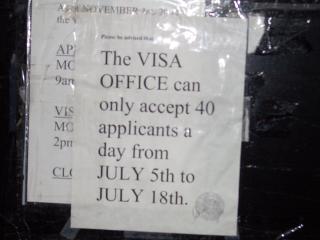從獨立紀念日長週末以來的一個星期左右,我一直處於「進行一個搬家的動作」的狀態──這個敘述是精確的,不可以修正成「我正在搬家」,或是「我搬家了」。因為實在是要搬不搬,搬了一半。大半家當已經移到新地方去了,自己卻仍然守著租約未滿的舊居,有一搭沒一搭地收拾剩下零碎的東西。如果把搬家這件事情寫成分解動作,應該可以概略分成四步驟:第一階段,打包裝箱;第二階段,搬動物件;第三階段,東西歸位;第四階段,打掃清理。而我當時的狀態則是分散於第一二三階段──客廳是第二階段,臥房是第三階段,浴室廚房還在第一階段,加上等著賣掉或丟掉的大家具還未處理,真是一團混亂。
從獨立紀念日長週末以來的一個星期左右,我一直處於「進行一個搬家的動作」的狀態──這個敘述是精確的,不可以修正成「我正在搬家」,或是「我搬家了」。因為實在是要搬不搬,搬了一半。大半家當已經移到新地方去了,自己卻仍然守著租約未滿的舊居,有一搭沒一搭地收拾剩下零碎的東西。如果把搬家這件事情寫成分解動作,應該可以概略分成四步驟:第一階段,打包裝箱;第二階段,搬動物件;第三階段,東西歸位;第四階段,打掃清理。而我當時的狀態則是分散於第一二三階段──客廳是第二階段,臥房是第三階段,浴室廚房還在第一階段,加上等著賣掉或丟掉的大家具還未處理,真是一團混亂。說來汗顏,高年級的研究生要搬家,通常都是學業已成要離開,所以好幾位學弟妹們聽說我在moving sale賣東西,開口就是恭喜學長,終於畢業了。可是我之所以搬家,正是因為學位未得,賃居已逾越住在學校宿舍的年限,必須強迫搬離。我知道這項政策本意應該是要把有限的住宿資源釋出,讓新來乍到摸不清楚狀況的新學生有窩棲身;不過對於修業時間超出預期而被強制搬遷的舊生而言,彷彿也是一種懲罰──已經給你這麼久時間了,怎麼不趕快把實驗了結、把論文寫好呢?把你趕出宿舍去!
如果不談這些尷尬的緣由與勞動的辛苦,搬家其實是一個清理門戶的好時機。如果沒有這樣強制挪動與打掃,根本不會知道原來在角落裡在櫥櫃內還有這麼多東西:有用的,沒用的,當初懶得丟的,一直捨不得拋棄的,不知道留下來做什麼的…,如今要裝箱打包,正是一件件重新檢視的機會。早先的不捨到現在或許已經完全不眷戀,平時狠不下心的也正有個冠冕堂皇的名目來絕情離棄。於是一袋袋垃圾就這樣神奇地現身,想像不到平日它們是如何隱身在週遭。
朋友說我是個惦著過去的人,對發生過的事情細節都記得清清楚楚──是嗎?或許我容易把物件當作提示,檢索岀堆疊在記憶深處的往事:那本圖畫書是當初要送卻終究沒能送出的遺憾、一對玻璃小咖啡杯標記著共處時日的點滴、幾乎沒用過的擀麵棍有著跨海細膩貼心的關懷、小陶杯則是我不能珍惜的直截與勇敢、而慵懶女聲的爵士樂CD唱著謹守分寸的短暫嘗試。我一邊收拾裝箱,一邊清理過去,用去比想像中還多的時間與精神。不過,這些總要分類打理好,否則一團混亂搬到新居,要真正安頓下來就更不容易了。
 再花時間,也是終要解決的.總算把滿滿一屋的物品清空,回復當初交到我手裡的空空蕩蕩。再巡視一次,確定房間櫥櫃以及冰箱裡都沒有東西,可以還回鑰匙了。最後,取出相機留影,關上窗子,關上門,結束。
再花時間,也是終要解決的.總算把滿滿一屋的物品清空,回復當初交到我手裡的空空蕩蕩。再巡視一次,確定房間櫥櫃以及冰箱裡都沒有東西,可以還回鑰匙了。最後,取出相機留影,關上窗子,關上門,結束。也是重新開始。